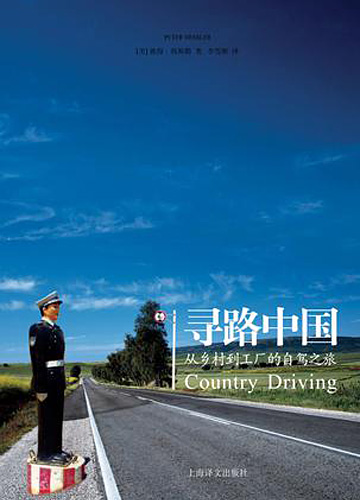中国大陆出版的 “ 寻路中国 ” 一书,由于政治原因,有些节段被检查删除。以下是全部被删除的字句。
每一单元均列出其原属某章的章名及第几页,同时也列出它在英语原著书中的章名及页数,以供参照。为便于读者查阅,先列出紧在其前的字句,随后以 “ 粗体印刷 ” 蓝色的 字体印出被删除的部分。
“城墙”
English title: “The Wall”
第二章
83 [page 85 in US edition]
. . . . 或站在展板跟前,摇晃着身子想读出那些印着的有关成吉思汗和元朝的文字。
展览材料上印着中文、蒙文和英文。跟中国许许多多的博物馆一样,这里的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。有一个英文句子,大意是这样的:
- 成吉思汗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。
- 跟它对应的汉语句子是这样的:
- 在中国历史上,成吉思汗是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。
在中国,人们把成吉思汗当成汉人加以谈论——至少从文化的角度看来是这样,因为他建立了王朝,统一了中国。在中国人的眼中,蒙古天然地应该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——直到1912年,这个地方一直处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。在二十世纪里,蒙古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,后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,而内蒙古仍旧在汉人的掌管之下。毛泽东掌握政权之后,他提倡汉人到这一地区定居。时至今日,汉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在80%以上。
汉人还牢牢地主宰着历史。在成吉思汗陵,并没有什么尸首,因为这位伟大的领袖的安葬地点尚不为人所知。历史学家们认为,那个地方应该在蒙古国境内。中国人在1950年代修建了陵墓,以象征着对内蒙古地区的掌控权。展板上的内容对蒙古人的历史做了倾向于汉人的描述:
忽必烈可汗——成吉思汗的孙子之一——建立元朝,使之成为疆域辽阔的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他发扬了中原地区的传统习俗。他主张改进生产方式,发展科学技术,以此来鼓励农业、手工业以及纺织业的发展。贸易和航海技术也得到了发展,加强了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。
陵墓的主建筑里陈列着一排棺椁,人们以为那是成吉思汗及其近亲属的棺椁。在陈列室外面,我碰到了在那儿上班的一个蒙古女导游。她问我是哪里人,听到我给出的答案,她若有所思地笑了笑。“美国很了不起呀,”她说,“跟曾经的成吉思汗一样。”
听到这里,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。跟曾经搭过我车的人一样,她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——染成红色的头发,戴着银制的耳环,穿着紧身牛仔裤。她二十四岁,颧骨很高,长着草原人特有的细长小眼睛。我还在想着她刚才说的了不起的美利坚合众国,她又说话了。
“这不是成吉思汗的陵墓,”她说,“我在这儿上班,但我还是想告诉你,那些棺椁里面什么也没有,没有人知道,他的陵墓到底在什么地方。还有,根据传统,应该有特制的物件,盛装他的灵魂。”
她列举了一些物件的名称,可我一件也没有听说过,于是,我让她在我的笔记本上把那些物件写出来。她盯着钢笔和笔记本无助地看了一会,说道:“抱歉,我喝醉了,写不出来。”
她领着我,即兴参观了那些陈列品,指出了其中的谬误和夸张不实之处。她告诉我,成吉思汗出生在蒙古国境内——这个细节对她来说非常重要。她认为,由于实行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,内蒙古已经酿成了生态灾难。“所以,北京每年春天都有沙尘暴天气,”她说,“再说,我们这个民族算是衰落了。我们曾经很了不起,可是现在呢,什么都算不上。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——有蒙古国,有内蒙古,俄罗斯还有个布里亚特。可是,曾经一度,我们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民族啊。我们跟汉人不同,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。蒙古人喜欢自由,但自由对汉人来说无所谓。你注意到了吗,蒙古人很会喝酒?”
我说我注意到了,其实我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。
“那是因为心情的关系,”她说,“落差这么大,心情当然不好。蒙古人对这一切无可奈何,所以,我们只好喝酒。”
我们走到了室外,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大地。我的视线越过陵墓的围墙,看到了一片干枯的灌木丛,风吹着那个女子的头发,遮住了她的脸。“当然,蒙古人在过去也杀了很多人,”她说,“可是,他们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进步是相当大的呀。就像希特勒——有人可能会说,希特勒这个人很坏,可是,他至少有能力领导一个国家。这一点,你不能否认吧。”
“你认为希特勒是好呢,还是坏?”我问她。
“好坏都没有关系,”她回答道,“我怎么判断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你可以叫他法西斯,或者别的什么名字,随你喜欢吧,可是他把名字留下来了。成吉思汗也是一样。曾经,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,现在的人们还是知道他。奥萨马·本·拉登也是如此。他袭击美国的时候,我替他和阿富汗人感到高兴。不是跟美国有仇,而是因为塔利班是一个弱小的族群,他们想引起别人的关注。现在,所有人都知道了奥萨马·本·拉登。他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,我就看重这一点。”
在风中,她走起路来有些摇摆的样子,她问我,是否可以找个地方坐一下。我们在陈列室外面入口处找了张凳子坐下来,在阳光里,她眯缝着眼睛,放松了下来。“我喜欢跟陌生人说话,”她说,“有的时候,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话还比较轻松些。今天说话这么轻松,是因为我喝醉了。我一般都没有醉得这么厉害,我说话一般也没有这么随便。但是,中国有很多让我不喜欢的东西。你跑到这个陈列室来,他们说成吉思汗是汉人的英雄,真是无稽之谈。跟他打仗的,就是汉人。这个陈列室纯粹是一堆垃圾。”
间或,有别的工作人员领着几个喝的醉醺醺的领导,从旁边经过,看到我们坐在一起,都笑而不语。可是,那女子似乎并不在意。“我第一次做导游的时候,”她说,“人们总要投诉我,因为我老是讲蒙古人——讲蒙古人当领袖,讲蒙古人打胜仗,讲蒙古人建立了帝国等等。他们想让我说成是中国人。于是,领导批评了我。所以,我现在只好说成是中国人,可我根本不这么看。即便如此,我讲的故事跟其他导游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。别人跟我说,我们讲的不一样。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个不一样,反正就是不一样。”
“也许,不一样之处就在于你说这个陈列室是一堆垃圾,”我这样说道,那个女子大笑起来。
“之所以不一样,是因为我跟别的人不一样,”她说,“我喜欢跟不认识的人说话,女孩子一般不会这么做的。我男朋友就不喜欢我这样。”
我们坐在一条凳子上,她一点点地向我这边挤过来,我甚至能感觉到,她的腿挨到了我的腿。她的呼吸越加急促了——有一股浓浓的白酒味。
“其实,”她告诉我。“我并不怎么喜欢我的男朋友。”
看起来,该换个别的话题才合适,可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她把我的脸庞仔细打量了一番,看着我的眼睛,终于问道:“你是不是特务?”
“不是,”我回答道,“我是个作家。我告诉你,我是写文章的,是写书的。”
她凑的更近了些。“如果你是特务,你可以跟我讲,”她压低了声音说,“我发誓,我不会跟任何人讲。”
“实话实说,我不是特务。”
“算了吧!”她说话的声音带一点恳求的味道。“你一个人来到这里,你会讲中文,你又来的是内蒙古这个地方,你还自己开车。你肯定是个特务。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么?”
“我跟你讲的,就是实话,”我回答道,“我不是什么特务。再说,特务怎么会来成吉思汗陵这个地方呢?”
她想了想,很有些沮丧的样子。“我一直都想碰到个特务,”她小声地说,“我好希望你真是个特务呢。”
那女子现在好像清醒了些,提出要把的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我笔记本上,万一我回来的时候用得着。她写得很认真,写了中文,写了蒙文,还画了一幅画。画的是一个太阳——大火球向四周发出光芒的图案,看上去十分天真。
“村庄”
English title: “The Village”
第二章
194 [page 202 in US edition]
. . . . 1990年代中期,这个村子跌倒了谷底:人口急剧减少,留着没走的人往往爱在乡邻之间搬弄是非,散布谣言。后来,当一些村民们开始练习法轮功这种吐纳柔体操的时候,事情才得以改观。那时候,法轮功这个东西新旧融合,让人耳目一新:它的发明者是个现代人,名叫李洪志,东北人,但他把道教、佛教,以及太极里边为大家所熟悉的很多东西揉在了一起。法轮功这个东西很难界定——从某些方面来看,它有点像一种宗教或者哲学思想,但它又有一些套路供大家锻炼身体之用。这一系列因素糅合在一起,创造出来的东西相当受人欢迎,尤其在经济陷入困境的北方更是如此。在三岔,练习者乐于看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一套新的体系出现,没过多久,又有很多人加入了进来。到1990年代末期,全村绝大多数人好像都在清早时分相聚到了断头路旁边的坝子上。曹春梅和魏子淇也成了虔诚的一份子,多年以后,她对那个时代依然津津乐道。“那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好处,”她对我说,“那段时间,魏子淇既没抽烟,也没喝酒,因为法轮功说不可以做那些事情。他那个时候也不大生气了。村里人好像个个都很高兴似的。整个上午,我们都聚在一起。”
后来,法轮功的影响范围波及到了每一个人,但缺乏明确的定义成了它在政治上的拖累。在中国,得到官方许可的宗教只有五种: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和基督教。各种信仰都要接受政府机构的监管,不允许存在独立的领导体系,例如,中国的天主教不能承认教皇的存在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李洪志就有问题,尤其在他移居美国之后更是如此。随着法轮功的影响越来越大,它招致的既有追随者,也有批评者。有时候,中国的一些记者会在媒体上抨击这样的修行行为,斥之为跟迷信没有什么两样。1999年4月,一篇批评性文章激起一万多信众在北京城内集会。他们以静坐示威的方式包围了中央政府所在地,要求得到认可。不出所料,他们受到了关注——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,首都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活动。随后的几个月之内,政府取缔了法轮功,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收到了惩处。
三岔没有人去北京参加抗议活动,但村民们很快便感受到了压力。村里面的党员——有些人在当初还是劲头十足的习练者——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会议,批判法轮功,早上在那块空地上进行的操练仪式也戛然而止。在中国,类似步调一致的全国性运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权威。当初作为新思潮的源泉,共产党也许是无产者的组织。但迄今为止,它的组织性和协调性依然完好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共产党很清楚,在以农村为主的国家,地方权力机构具有怎样的重要性。从北京发出的命令,会在顷刻之间传递到无数个居民点。即使在农村地区,也没有哪个居民居住在村级政治影响力的范围之外。我去拜访三岔村的隐士马玉发的时候,他说他不知道当今中国的领导人是谁。但当我问他谁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的时候,他立马就能够给出答案。他知道她的名字,他也知道她丈夫的名字,他还给我讲了她丈夫和魏家的关系。在中国的农村,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政治要素。1999年之后,这些政治要素全都反起了法轮功。
全国上下,这样的镇压活动往往是非常残酷的。根据一些人权小组提供的情况,几百名信徒死于监禁期间,因为警察常常会滥用权力,以说服他们改变信仰,或承诺放弃修行。被送到劳改农场的又有几千人之多。不过,最先的习练者数量多达千万,他们绝大多数人只需要下决心不再参与即可。在三岔,据我知道,只有一个村民拒绝放弃这一全新信仰,在怀柔看守所呆了一个星期才彻底改变了想法。
194 [page 204 in US edition]
. . . . 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,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,而是因为他们想藉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和共担。对法轮功的取缔之所以非常成功,这是原因之一——共同体一旦被粉碎,大多数人也就找不到再坚持那个信仰的理由了。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经历让他们学会了耐心,他们知道,什么时候肯定还会再有别的什么东西出现的。
“工厂”
English title: “The Factory”
第三章
379 [page 393 in US edition]
. . . . 真正紧要的,在于抗议的目标。如果人们是要求推翻共产党,或者抗议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结构,那问题就严重了.